中世纪美学(美是上帝的属性)
中世纪
中世纪(The Middle Ages),指从公元5世纪后期到公元15世纪中期。欧洲历史三大传统划分:古典时代,中世纪,近现代;中世纪是指其中的一个中间时期。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终于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最终融入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中。中世纪历史自身也分为前、中、后期三个阶段。术语“黑暗时代”、“黑暗时期”一般指中世纪早期。
从第四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一千年左右漫长的时期中,欧洲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如果说还有些活动,那也只是把普洛丁所建立的新柏拉图主义附会到基督教的神学上去,一直到但丁,这种停滞的局面才开始转变。
宗教背景
基督教发源于住在巴勒士坦的希伯来民族,是对于希伯来旧教(犹太教)的一种改革。巴勒士坦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省,地瘠民贫,受剥削特别沉重,基督教的创始人宣扬在终会到来的天国里,人们一律平等和互相友爱,反对家庭制度,私产制度和世俗政权,本来带有反抗罗马帝国的意味。这是一种穷苦人的宗教,代表当时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的希望。它之所以能在罗马帝国里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就因为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深广的心理基础。在基督教开始传播的头三百年里,它不断地遭到罗马政权的残酷的迫害和镇压,有时只能在地下活动。但是它的传播并不因此停顿,反而蔓延得更深更广,深入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从三世纪以后,罗马政权开始改变政策,以利用代替镇压,到了第四世纪,就把基督教正式定为国教,��并且下令禁止其它的宗教信仰,罗马政权想利用基督教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来牢笼复杂的被统治的多民族,使他们有一种思想信仰上的统一,便于维持罗马政权。宗教本是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他们安分守己,这对于维持罗马政权是有利的。
从三九五年东西罗马帝国分立之后,基督教会也就逐渐分成东西两教会。东教会叫做“正教”,西教会叫做“天主教”。跟中世纪欧洲政局和文化特别有关的是西教会。从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几百年之中,罗马教皇就由天主教会的首领变成同时是世俗政权的首领。天主教会对于封建制度的奠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本身变成极大的封建地主,拥有全欧土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教会的官阶也是按封建等级制来分的。为着维持罗马教廷的封建统治,教会还制造出“神权说”,作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据说世俗政权是由上帝授予的(上帝是最高的封建主),教皇是上帝在尘世间的代理人,代上帝把政权以及政权所统辖的土地人民授予国王,国王以下各等级的权益也是这样由上一层递授予下一层,一直到最下层的农奴。国王加冕应由罗马教皇主持,这就是“封”。受封的国王就变成教皇的隶属或佃户(vassal)。800年查理大帝受教皇的“封”,就标志着封建制度的正式奠定,“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以及宗教与封建政权的联盟。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成立也标志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查理大帝所统辖的疆域就是近代法德等国的摇篮)以及世俗政权的重新抬头。此后数百年的历史便成为教廷与世俗政权之间勾结和冲突的历史。到了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工商业日渐发达,人民的力量日渐抬头,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日益尖锐;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近代资产阶级起来了,封建和教会的势力才日渐削弱。
中世纪的经济穷困,生产落后,政治腐败,故争频繁,以及社会动荡不宁的情况都是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当时统治一切的教会对于世俗文化是极端仇视的。凡是教会认为是违反自己的教义和利益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异端”的罪名和残酷的镇压。对于一般人民,教会所采取的是愚民政策,不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中世纪在很长时期里,仅有的学校是寺院中训练僧侣的学校(后来的巴黎,牛津等大学都是由僧侣学校发展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僧侣是唯一的受教育的阶层,一切有关文化的事都由僧侣垄断。许多声名煊赫的国王和贵族骑士都是文盲,其他可想而知。当时唯一的通用的官方语言是拉丁,圣经是用拉丁文本为官方定本,礼拜仪式和宣讲教义都用拉丁文进行,而拉丁文也是僧侣阶级的专利品,普通人民所说的地方语是受鄙视的。
天主教会要扼杀世俗文化教育,因为它认识到世俗文化教育在当时只能是根深蒂固的希腊罗马古典的文化教育,而这种古典文化教育和基督教所宣扬的教义是不共戴天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神权中心与来世主义。现世据说就是孽海,一切罪孽的根源在肉体的要求或邪欲。服从邪欲,灵魂就会堕落,就会远离上帝的道路而遭到上帝的严惩。所以人应当抑肉伸灵,抛弃现世的一切欢乐和享受,刻苦修行,以期获得上帝的保佑,到来世可登天国,和上帝在一起同享永恒的幸福。来世主义是与禁欲主义分不开的;现世的禁欲是为着来世的享乐。“归到神的怀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这就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种教义是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长期扎根的地区里传播开来的,它一开始就把自己作为古典文化的鲜明的对立面而提出,就和古典�文化所代表的理想进行顽强的斗争。古典文化代表哪些理想呢?古典文化是建筑在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基础上的。“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希腊罗马虽然也信神,但是他们的多神教还是根据人的生活和人的需要来建立的。他们理想中最高的善”是现世的幸福,并不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他们要求灵与肉的平衡发展和多方面的自由活动,如体育锻炼、学术探讨和文娱活动等等。就是这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古典文化,基督教要把它连根拔掉,代之以它自己的神权主义和来世主义。在基督教会看,人当满足于对上帝和基督教义的信仰,只有这个才是真理,此外一切知识欲都是无用的,有罪的,应当一律压制下去,否则人们就会落到“邪教”的圈套里,这就等于把灵魂交给魔鬼。就是为了防止“邪教”的复辟,基督教会才想尽一切方法,去禁止世俗文化教育的活动。
基督教会仇视一般文化教育活动,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假如反对文学和艺术的论调也算是文艺理论,基督教会也就有一套文艺理论。基督教会攻击文艺的理由和柏拉图所提出的大致根同,就是文艺是虚构,是说谎,给人的不是真理;并且挑拨情欲,伤风败俗。
中世纪美学思潮——“美是上帝的属性”
尽管基督教对文艺是仇视的,它所传播的区域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植根很深的区域,而且它本身也还要利用文艺为宗教服务,它就不能不有一套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来抵制古典的、“邪教”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并且为它所利用的宗教性的文艺作辩护。当时所谓“经院派”学者都属僧侣阶级,对一切问题都是从宗教的角度去看,所以把一切学问都看成神学中的个别部门,美学也是如此。
中世纪欧洲有一股始终一贯的美学思潮,就是把美看成上帝的一种属性,上帝代替了柏拉图的“理式”,上帝就是最高的美,是一切感性事物(包括自然和艺术)的美的最后根源。通过感性事物的美,人可以观照或体会到上帝的美。从有限美见出无限美,有限美只是到无限美的阶梯,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在美的自然事物与艺术作品之中,经院派学者一般是看重前者而鄙视后者,因为前者是神所创造的而后者只是人所创造的。“人造的”就含有“虚构的”“不真实的”意味。虔诚的教徒们要“从上帝的作品中去赞美上帝”。因此,中世纪的美学并不以文艺为主要对象。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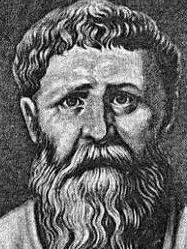
圣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在还未皈依基督教以前,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学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当过文学和修词学教师,写过一部美学专著,题为《论美与适合》,手稿在当时就已失传。皈依基督教后,他一方面钻研基督教经典,一方面仍继续研究他早年所爱好的柏拉图。他的美学言论大半见于他的神学著作和《忏悔录》。
圣奥古斯丁给一般美所下的定义是“整一”或“和谐��”,给物体美所下的定义是“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再加上一种悦目的颜色”。前一个定义来自亚理斯多德,后一个定义来自西赛罗,在字面上都只涉及形式。但是这些侧重形式的老定义在圣奥古斯丁的思想里是和中世纪神学结合在一起的。无论在自然中还是在艺术中,使人感到愉快的那种整一或和谐并非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而是上帝在对象上面所打下的烙印。上帝本身就是整一,他把自己的性质印到他所创造的事物上去,使它尽量反映出他自己的整一。有限事物是可分裂的,杂多的,在努力反映上帝的整一时,就只能在杂多中见出整一,这就是和谐。和谐之所以美,就因为它代表有限事物所能达到的最近于上帝的那种整一。但是由于与杂多混合,比起上帝的整一,它究竟还是不纯粹不完善的。从此可见,圣奥古斯丁关于无限美(最高美、绝对美)与有限美(感性事物的美,相对美)的分别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柏拉图的看法(感性事物的美只是理式美的影子)。
圣奥古斯丁还提出丑的问题。有限世界在本质上虽是杂多的,却具有上帝所赋予的整一或和谐。丑的事物(包括罪恶在内)在这和谐整体里占什么地位呢?圣奥古斯丁认为美虽有绝对的而丑却没有绝对的。丑都是相对的,孤立地看是丑,但在整体中却由反称而烘托出整体的美,有如造型艺术中阴阳向背所产生的反称效果。这就是说,丑是形成美的一种因素。因此,丑在美学中不是一种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范畴。圣奥古斯丁还指出一个人能否从差异部分的统一中见出和谐,要看他的资禀和修养何如。要有合拍的心灵,才能认识到整体的和谐;否则只见到各个孤立的不同的部分见不出整体及其和谐,就觉得某些部分丑,甚至全体都丑。
St. Thomas Aquinas (圣托马斯·阿奎那)
圣托玛斯(St.Thomas Aquinas,1226——1274)是基督教会公认的中世纪最大的一位神学家。他的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神学大全》。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和圣奥古斯丁一致的,也是把普洛丁的新柏拉图主义附会到神学上去,不过他同时也接受了亚理斯多德的影响。
原文: 美有三个因素。第一是一种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其次是适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是鲜明,所以着色鲜明的东西是公认为美的。 人体美在于四肢五官的端正匀称,再加上鲜明的色泽。 美与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二者都以形式为基础,因此,人们通常把善的东西也称赞为美的。但是美与善毕竟有区别,因为善涉及欲念,是人都对它起欲念的对象,所以善是作为一种目的来看待的;所谓欲念就是迫向某目的的冲动。美却只涉及认识功能,因为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的。所以美在于适当的比例。感官之所以喜爱比例适当的事物,是由于这种事物在比例适当这一点上类似感官本身。感觉是一种对应,每种认识能力也都是如此。认识须通过吸收,而所吸收进来的是形式,所以严格地说,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
理解: 第一,“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的”。这个定义指出美是通过感官来接受的,美的东西是感性的,美感活动是直接的,不假思索的,也就是说,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内容意义的。这种强调美的感性和直接性的观点在后来康德和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就是美只关形式不沾概念说与艺术即直觉说的萌芽。
第二,在指出美与善一致的同时,圣托玛斯又指出美与善毕竟有分别,这分别就在于善是欲念的对象,欲念所追求的目的不是立即可以达到的;美是认识的对象,一认识到,就立刻使美感得到满足。对于对象并不起欲念,这也就是说,美没有什么外在的间接的实用的目的。这样把美与善的区分归结为带不带欲念和有没有外在目的的区分,对后来唯心主义美学的发展也很有影响。这就是康德的“审美判断的二律背反”说的萌芽,康德也认为美不关欲念,无外在目的。
第三,圣托玛斯在各种感官之中只承认视觉和听觉为审美的感官,其理由有二:第一,视觉与听觉“与认识关系最密切”,是“为理智服务的”,而审美首先是认识活动。其它感官如味觉嗅觉等所得到的快感等则主要是欲念的满足,生理方面的动物性的反应。其次,“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形式只能通过视觉和听觉去察觉。这种看法的重要性有两点:它是寻找美感与一般快感的分别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而且确定视觉和听觉为专门的审美感官,这对后来美学的发展也起了一些影响,例如达·芬奇认为视觉更高于听觉,因此断定绘画(通过视觉)更高于诗歌音乐(通过听觉),莱辛根据视觉和听觉的分别来确定绘画与诗歌的界限。
第四,最突出的是圣托玛斯的形式主义的观点几乎与圣奥古斯丁的完全一致。他所指出的美的三个因素:完整、和谐与鲜明都是形式的因素,所以他说“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中世纪经院派学者们谈到美,大半都认为美只在形式上,很少有人结合到内容意义来讨论美。在这一点上康德在《美的分析》中也是与中世纪经院派学者一致的。此外,康德的在美感中“各种官能和谐地发挥作用”的说法在圣托玛斯的美学观点里也已有萌芽。“感官喜爱比例适当的事物,是由于这种事物在比例适当这一点上类似感官本身”,这就是说,美的事物和感官本身相应,所以合拍。
第五,在美的三个因素之中,完整与和谐是从希腊以来美学家们一向就着重的,圣托玛斯结合到西赛罗和圣奥古斯丁所提到的颜色,另提出“鲜明”一个概念(他用了许多同义词,如“光辉”“光芒”“照耀”“闪烁”之类)。在运用这个概念中他把美归结为神的特性。他给“鲜明”所下的定义是: 一件东西(艺术品或自然事物)的形式放射出光辉来,使它的完美和秩序的全部丰富性都呈现于心灵。 这种光辉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是“活的光辉”,世间美的事物的光辉就是这种“活的光辉”的反映,所以人从事物的有限美可以隐约窥见上帝的绝对美。
圣托玛斯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大成,也是经院派哲学的殿军,上承新柏拉图派的神秘主义,下启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美学。他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他的美学思想正如他的政治思想一样,以维护天主教会的反动的封建统治为主要目的,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仍然可利用来作为维护法西斯统治的思想武器。以玛里坦(Maritain)的《艺术与经院哲学》一书为代表的新托玛斯主义美学在法意美英等国还有相当广大的市场,便是一个明证。
参考资料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